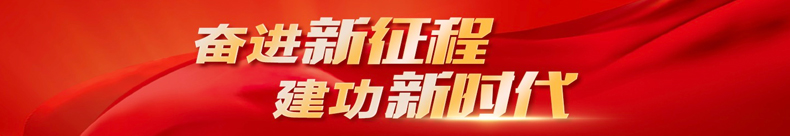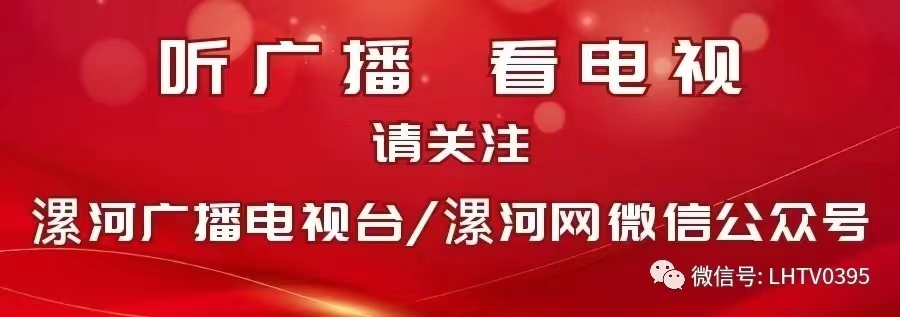中央電視臺大型專題片《復興之路》解說詞連載——
上篇:雄關漫道真如鐵
五、風云激蕩
1912年8月24日,北京前門火車站人群如潮,人們在等待一位已不在位的總統,盡管他僅僅做過4個月的臨時大總統,但人們仍然愿意以歡呼和掌聲對他致以敬意。
下午5時30分,禮炮聲聲,歡快的樂曲中稚嫩的童聲唱起了歡迎的歌兒。當孫中山出現的時候,掌聲雷動,人們拼命揮舞著手中的旗幟和帽子。孫中山坐上袁世凱金碧輝煌的朱漆金輪馬車,由30位騎兵開路,從正陽門直人外交部街迎賓樓。當晚即與袁世凱會晤。20多天里,他們會晤達10余次。9月16日,孫中山、袁世凱、黃興共同制定《政治綱領》,為民國的建國方案。
綱領一定,孫中山和黃興認為中國必興,他倆興沖沖地南下履行對共和國的使命。孫中山雄心勃勃地要為中國建設20萬里鐵路;黃興則回到南京,解散了南方數十萬部隊之后,解甲歸田。
中國的未來似乎一片光明,人們期盼著國家的富強和生活的美好。然而,共和的天空下陰云密布,封建余脈仍在人心盤桓,無盡的野心和權欲攪得神州大地周天寒徹,將中國卷入了新的危機和亂局。
亂局如麻,希望如何破繭而出?
(一)再添國恥的竊國賊
1913年3月21日晚,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受總統袁世凱邀請前往北京“共商國是”。就在宋教仁躊躇滿志地要登上火車,為中國人謀求一個輝煌未來的時刻,突然三聲槍響,宋教仁倒在了地上。黃興、于右任、廖仲愷等人急忙將他送往醫院。可惜彈中要害,到22日凌晨,終告不治,終年32歲。
臨死之前,血泊中的宋教仁致電袁世凱,請求他開誠布公地保障民權,確定憲法,那么,他“雖死猶生”。
宋教仁之死使舉國大嘩,不久,殺宋教仁的兇手應夔丞(字桂馨)、武士英落網,又牽連出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多份電報表明此案與國務總理趙秉鈞有關。趙秉鈞、應夔丞、武士英在1年內紛紛命赴九泉。那么是誰在幕后操縱一切?能讓國務總理作替罪羔羊的又有幾人?
隨著案情的逐步明朗,黃興在當年4月13日將心中的憤慨凝成一聯:
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
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
袁世凱為什么必欲除宋教仁而后快呢?早在袁世凱在北京繼任臨時大總統時,南方的議員們為制約袁世凱,就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了作為內閣制的政府,總統為元首,由總理處理國家事務,對國會負責。宋教仁正是這一制度的積極倡導者。
他聯合五黨組建國民黨,積極推進議會民主,鼓吹政黨政治,認為通過議會競選,“就可以組成一個黨的責任內閣……那么,我們的主義和政綱,就可以求其貫徹了”。
為此,他拒絕了高官厚祿的收買,堅守信念,就這么坦坦蕩蕩地南下,去傳播民主政治的理念,卻沒有覺察到背后陰冷的目光中萌動的殺機。
宋教仁奔走各省,經湖北、安徽、上海、浙江,到處宣傳民主政治,抨擊時政,針砭當局,在當時刮起了一陣民主政治的小旋風。他毫不避諱地指出袁世凱假共和的事實,被袁世凱得知后曾怒罵其“口鋒何必如此尖刻?”但后來歷史發展的事實表明,宋教仁的話正中袁世凱痛處,他所擔心的問題一一發生。宋教仁正是因為擔心會發生這些不可測的惡果,才極力推動政黨政治以鉗制袁世凱。
宋教仁的才華的確收獲了豐碩的果實,他使國民黨在參眾兩院獨得多數席位,本來已經勝券在握。他的憲政救國方案似乎也指日可待,他認為10年后,中國將富強,亞洲可以保持和平,甚至“世界全體亦受利不淺矣"。
袁世凱本很欣賞宋教仁,希圖收歸門下,但宋品行高潔、軟硬不吃,竟沒有一點縫隙。袁世凱于欣賞之余多了幾分畏懼。他是一世奸雄,終生圍著權力打轉,本來自恃北洋精銳在手,沒把議員們的活動太當回事,但一見宋教仁等竟敢制定法律制約他,玩起了歐美式的政黨政治,也有些著慌。他決不愿做一個“虛君”,也決不會坐視頭上總是懸著《臨時約法》這柄劍,更不甘心到手的至高權力又飛了。他與宋教仁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因為兩個人的理念和品性實在相差太遠。
既然無法收買你,那就消滅你。于是上海火車站的槍響了。
孫中山、黃興聽到宋教仁之死訊,始驚復怒,緊急籌劃對策。但在采取法律手段還是訴諸武力的問題上爭執不下。此時,袁世凱已經開始動手了,他先是不經國會批準擅自向五國銀行團借款2500萬為軍費,又以大將段祺瑞代替趙秉鈞組成戰爭內閣,之后公開發電嘲諷孫中山和黃興無能。國民黨人發現已無路可走,南方幾省通電討袁,開始二次革命。可惜倉促之下,又無能戰之將,不到兩月,紛紛敗北。開國元勛們又成了“通緝犯”,孫中山項上人頭價值20萬。
袁世凱先是利用武力挾持和饑餓壓制的手段,當選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后又發布解散國民黨令,國民黨籍議員一律被驅逐出國會。1914年1月10日,第一屆正式議會被袁世凱正式解散。《臨時約法》也被廢除,袁世凱宣布總統不僅可以無限期連任,還可以推薦繼承人,這與皇帝還有多大區別?
就這樣,在西方似乎行之有效的普選制、議會制、多黨制一到中國全變了樣。宋教仁死后,雖然國民黨擁有多數席位,但議會仍然成了袁世凱手中予取予求的“玩具”,所謂的民主和制衡都成了美麗的神話。
“政舉人存,人亡政息。”這一言道盡宋教仁身后功業的幻滅。但這是20世紀中國資產階級救國方案的一次實踐,雖然失敗了,它卻推動著中國人尋找更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宋教仁的理想,是20世紀留給中國人的一筆重要精神遺產。
(二)護國戰爭:討逆者怒而奮起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晉見民國總統袁世凱,親手將一份秘密文件交給袁世凱,袁世凱“大驚,一時難以答復”。這份秘密文件就是“二十一條”。
“二十一條”的內容狂妄而大膽,但這些內容是日本當局仔細斟酌考慮的結果,而且拋出“二十一條”的時機也非常好,此時的歐洲已經打成了一鍋粥,英、法、俄與德、奧分為兩個陣營,互相廝殺,哪里顧得上東方?
但其條件之苛刻、野心之巨大,即使日本人以支持袁世凱稱帝為交換,袁世凱也不敢輕易答應。在今天天津歷史檔案館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當年袁世凱對“二十一條”的批注:各條內多有干涉內政、侵犯主權之處,實難同意。
為引起世界注意,中國政府故意將部分內容外泄,也未能換來國際同情。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凱政府遞交最后通牒,在山東增兵3萬,以戰爭手段恐嚇中國。段祺瑞表示要以武力抗爭,但袁世凱以國力衰弱為名拒絕,政府大員們紛紛迎合袁世凱的意見。5月25日,袁世凱政府在修改后的“二十一條”上簽字。日本為之舉國狂歡。
這是中國人的奇恥大辱。人人皆知這是日本圖謀中國的關鍵一步。被袁世凱通緝并懸賞捕殺的國民黨元老黃興等人呼吁黨內同志,“暫停革命,一致對日”。上海數萬人集會抗議。北京各校學生每日課余誦最后通牒一遍,以示不忘國恥。有的青年學生因而自殺,有的斷指寫血書,有的要求入伍。全國教育聯合會決定,以5月9日為“國恥紀念日”。民國已經建立了3年,但中國人依然沒有看到前方的出路。
就在民國初立之時,外蒙古地區180多萬平方公里脫離中國,民國政府對此無能為力。
四面楚歌的情形并沒有多少改變,外國的戰艦仍在中國內河航行,列強在華特權原封不動,租界和占領區依然如故。日本漸成中國心腹大患,試圖把中國變成殖民地的野心日益膨脹,如虎在側,眈眈窺視,成為中國最危險的敵人,令國人寢食難安。
中國的問題決不僅僅是外患。
1912年,隨著中國最后一個皇帝的退位,封建制度在中國壽終正寢然而,中國人民所預期的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卻沒有到來,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顯然不能拯救危機深重的中國。他們關注的是權勢和富貴,最好能像中國古代封建帝王那樣面南坐北地統治“天下”。
人民在民國也沒有體會到什么自豪與幸福。普通的人民關注的是遍及各地的兵變,連北京、南京、沈陽這樣的大城市都無法幸免,當時的報刊上常見的描述是“大肆劫掠,慘不忍言”,人民生活在恐懼之中。
國際貿易多操縱于各國租界,商人們注重短期利潤,很少有人關心國家的長遠發展和人民生活。
李大釗在1913年寫的《大哀篇》中沉痛地指出:“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而這一切,不過是剛剛開始。
“二十一條”也曾使袁世凱痛徹肺腑,然而,袁世凱雖然沒有忘記國恥,但也沒有忘記已經落后于時代的野心,他不僅因為日本人暗示支持他稱帝而批準“二十一條”,還因“二十一條”之事得出結論,認為中國的屈辱是因為缺少一位皇帝。不久,應該發生在千年前的黃袍加身的把戲竟在已經實行共和的華夏大地上演。
1915年,各種支持袁世凱稱帝的中外學者的言論實在是太駭人聽聞了,一時間人心惶惶難安。8月,楊度、劉師培、嚴復、胡瑛、孫毓筠、李燮和等人組織籌安會,6人中有名滿天下的學者,也有老革命黨人,而他們此時所主張的竟是恢復帝制。9月2日,籌安會組織請愿團,向參議院請愿變更國體。
但是在眾多的勸進聲外,有更多的聲音在斥罵這逆流而動的丑行。晚清時的立憲派梁啟超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筆鋒直指楊度的謬論。《亞細亞報》懸賞3000元征文反駁梁啟超,竟無人敢應。更有不少人將所謂“籌安六君子”告上法庭,但在當局的壓力下,楊度等人平安無事,總檢察廳廳長辭職。
就連北洋大將段祺瑞、袁氏好友徐世昌、次子袁克文都不贊同袁世凱稱帝之舉。然而就在這滔滔反對聲中,袁世凱于12月12日接受帝位,改元洪憲,登上了他夢寐以求的皇帝寶座,也掘下了逆流而動的墳墓。
此時的他已經忘記了孫中山在就任臨時大總統的當天,曾表示要讓位于他的赤誠;此時的他也已經忘記了當年逼清帝退位后自己通電南京“水不使君主政體再行于中國”的電文。言猶在耳,逆行已肆。只是神州自有豪杰在,哪里容得他放肆胡為?
12月19日,一位將軍經過1個多月的艱難跋涉,輾轉各地,終于抵達昆明。他叫蔡鍔。
辛亥革命時,蔡鍔本為新軍協統。武昌義旗一舉,他就在昆明響應,年方30即為云南都督。對于袁世凱,他向來敬重。宋教仁之死令蔡鍔對袁世凱心生不滿,曾通電譴責,但他也反對國民黨訴諸武力,希望保持來之不易的和平。
袁世凱卻對蔡鍔深懷戒心,1913年10月,令蔡鍔赴京。蔡鍔知道北京是是非之地,于是韜光養晦,流連風月場所,以釋袁世凱之疑。隨著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日益表露,他與老師梁啟超商量對策,兩人分工協作,梁啟超作文反對袁世凱稱帝,就是引領輿論、給袁世凱當頭一棒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而蔡鍔的任務則是暗中聯絡各部,組織軍事力量以護衛共和國。蔡鍔不僅組織起了舊部,甚至還與袁世凱的重將段祺瑞、馮國璋等人暗通消息,達成默契。
蔡鍔曾與梁啟超相約:“事之不濟,吾儕死之,決不亡命;若其濟也,吾儕引退,決不在朝。”師徒二人決意以死捍衛共和政體,成功的話也是功成身退。其氣節之昭昭,令人感動。
1915年11月中旬,蔡鍔在小鳳仙的幫助下逃出北京,幾經艱難,終于抵達昆明。對于蔡鍔的行動,袁世凱感嘆說:“此人之精悍遠在黃興及國民黨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能匹。”蔡鍔成為袁世凱稱帝最大的敵人。
剛到昆明不久,蔡鍔即在昆明護國寺重招舊部,舉行起義,成立中華民國護國軍政府,隨后蔡鍔率軍北上,以不足兩月的給養與袁世凱派出的十數萬部隊鏖戰數月。到后來,即使“衣不蔽體,食無宿糧”,蔡鍔也毫不退縮。他抱定必死之心,將所有的才智激發出來,以一支孤軍在戰場上占據優勢。
蔡鍔義旗一展,各地紛紛響應,反對帝制的呼聲響徹中華大地。甚至,袁世凱曾經的心腹部下馮國璋也聯合江西將軍李純、湖南將軍湯薌銘、浙江將軍朱瑞、山東將軍靳云鵬等聯名通電,要他“取消帝制,以安人心”。
1916年3月,走到眾叛親離之絕境的袁世凱宣布取消帝制,他只做了83 天的短命皇帝,就又做回大總統。可是,人們哪里能容得他如此視國家命運如兒戲,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罵聲不絕之下,袁世凱死于1916年6月6日。副總統黎元洪繼任。據說袁世凱死前亦有悔意,曾作遺書一封云:“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
袁世凱至死才想起日本之威脅、共和之重要,整個中國卻已經為他的野心創痛傷重了。
保護共和政體的事業成功了,而作為領導者的蔡鍔身患重病,于1916年的冬天逝于日本福岡大學醫院,年僅34歲。黎元洪派特使護送蔡鍔遺體歸國,并舉行國葬。
英雄壯年逝,使人扼腕哭。梁啟超在挽聯中寫道:“國民賴公有人格,英雄無命亦天心。”
宋教仁的死,成就了袁世凱的竊國之行;蔡鍔的死,襯得中國的政局更加昏暗。
此時的中國是野心家的天堂,有共和之名,而無共和之實,共和成了一塊招牌。民國的政壇從此亂不可言,張勛復辟,曹錕賄選。
軍閥們你方唱罷我登場,一幕幕丑劇接二連三上演。名義上有國民政府,實際上是軍閥割據,到了后來,從占據半個縣到獨霸一省或幾省,陰謀與政變、戰爭與混亂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城頭變幻大王旗”是最常見的場景。
悲憤的孫中山一次次在南方發動革命,以推翻北洋軍閥。10余年里,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到死也沒有看到打倒北洋軍閥那一天。辛亥革命的功臣蔡濟民寫下詩句說:“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許多人從推翻清政府的盲目樂觀中清醒過來。怎樣才能救中國?這是那個時代每一個愛國者所思考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求索在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掀起了波瀾澎湃的時代大潮。
茫茫神州,路在何方?
此時,種種救國學說在中國大地應運而生,諸如教育救國、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甚至軍國主義救國等紛紛出現。在1915年,大多數人并沒有意到上海一份刊物的誕生。
(三)新文化運動:近代史上的百家爭鳴
1915年9月15日,也就是“二十一條”引起的怒潮未消,而袁世凱稱帝又甚囂塵上的時候,《青年雜志》創刊于上海黃浦江邊。辛亥革命時擔任過安徽都督府秘書長的陳獨秀在創刊詞《敬告青年》中號召國人建設一個青年中國,這個中國應當具有六個特點: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在這個昏亂的時代,尤其是帝制對共和的反撲使陳獨秀等一大批知識分子意識到中國的問題不是簡單的政治革命可以解決的。陳獨秀認為在中國搞單純的政治革命沒有意義,要想“救中國、建共和,首先得進行思想革命”,使人們從封建思想的束縛中解脫出來。
思想革命漸漸成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共識。一場文化啟蒙的運動終于在中國展開。
1916年,《青年雜志》改名為《新青年》。《新青年》在新青年中大行其道,但有趣的是,這一切頗得力于一位老翰林。
1917年1月4日,在一場大風雪中,北京大學迎來了新校長蔡元培。出人意料的是,這位新校長毫無官僚氣,他以一個平民的姿態走進中國的最高學府,也走進了中國歷史。中國知識分子也開始從廟堂走向民間,從官場走向象牙之塔、十字街頭。
為推翻清政府,這位光緒皇帝御筆欽點的翰林曾經為革命黨制造炸彈,但新生的民國讓他失望。他秉持教育救國的理念,希望能通過改造一所墮落的大學,用教育和啟蒙的方式為中國培養人才。
剛進北大,蔡元培就宣布了“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厲行改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力排眾議,聘請沒有高等學歷的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
陳獨秀將《新青年》主要撰稿人、26歲的胡適也聘為北大教授,魯迅等人也開始在《新青年》上嶄露頭角。由此開始,當時中國第一流的學者紛紛進入北大,北大擁有了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辜鴻銘、劉師培等一大批優秀的教師。
美國學者莫里斯認為,聚集在《新青年》周圍的知識分子的重要性是很難估價的。他們的著作鑄成了一代年輕學生的信仰和態度,1919年五四運動后,這些學生是政治上的生力軍,并成為現代中國革命的領導者。
蔡元培指出:“無論為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有理,持之以故,尚不達到自然淘汰之命運,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也許就是這種寬容造就了百家爭鳴的北大,也進一步在中國激起了新文化運動的浪潮。
1916年初,《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篇重量級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事”主張: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這就是改革文學的“八不主義”。《文學改良芻議》也因此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聲響亮號角,作者胡適被稱為“首舉義旗的急先鋒”。
他認為:“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有活的工具……有了新工具,我們方才談得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但是在當時,胡適的主張是受爭議的,甚至他的一些好友對其主張也“頗不以為然”。但胡適始終不免棄,對朋友們說“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白話文由他開始,后有了郭沫若的《女神》、徐志摩的《康橋》、俞平伯的《冬夜》等。白話文開始逐漸為國人所接受,一大批文學家開始用白話文表情達意,而這其中魯迅的《狂人日記》作為中國第一篇用白話寫成的小說,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地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魯迅用狂人的口說歷史的真面目,并用“救救孩子”向整個中國發出呼吁,號召人們群起反封建,而這正是新文化運動最主要的任務。
新文化運動意味著中國人開始對古老中國的傳統觀念進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并使中國的文化精神為之一變。中國人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反省從沒有如此深入過,而同時引發的社會影響也從未如此廣泛過。婦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號發展到實際行動,使新文化運動觸及的社會面遠比辛亥革命更為廣泛、更為深入。
1919年1月15日,陳獨秀在《新青年》上豎起了兩桿大旗—德先生、賽先生,也就是民主與科學。民主與科學使當時的青年如獲至寶,中國文化界也為之氣象一新。孫中山先生贊嘆這是“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德先生、賽先生成為中國此后10余年間人們耳熟能詳的名詞,也成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旗幟和精神遺產,正是在對民主與科學的不懈追尋中,中國人開始尋找到走出困境的方略。
(四)五四運動:新青年放聲高歌
1917年,此時的世界時局很令中國人高興。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派出20萬華工參戰的中國成了戰勝國。中國人為這一勝利而歡欣鼓舞。
1918年11月18日,新任大總統徐世昌在故宮太和殿廣場舉行閱兵式慶祝勝利。
人們將“克林德碑”拆除,改建為“公理戰勝”牌樓。一時之間,“公理戰勝強權”、“勞工神圣”、“民族自決”的呼聲撥動著每一個青年的心弦。人們希望可以用戰勝國的身份從列強手中收回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挽百十年國際上之失敗”,“與英、法、美并駕齊驅了”。
1919年1月,中國代表團向巴黎和會提出了7項要求,希望撤退外國軍隊、歸還租借地和租界,后來在民眾壓力下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條”的陳述書。
然而,在那個時代,公理并沒有向中國人民招手,勝利與弱國無關。中國人民的希望變成了失望。真正的勝利者是美國和日本。
巴黎和會決定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同時拒絕取消“二十一條”。巴黎和會給中國的只有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時,德國從中國搶走的天文儀器。
5月1日,上海《大陸報》登載了一個消息:“關于索還膠州租借之對日外交戰爭,業已失敗。”
中國被怒火點燃了。
5月3日晚,北大禮堂內擠滿了青年學生,有人以血書寫四個大字:“還我青島。”不少人還寫下了遺囑。他們相約第二天舉行示威,以表達憤慨。
5月4日,下午1點,天安門金水橋前匯集著來自北京各高校的青年生,金水橋對而飄揚著血書“還我青島”,旁邊還有一副對聯:
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
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頭。
隨后,學生開始游行示威,2萬份《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出現在北京頭,上面赫然醒目的幾行大字: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悲愴的呼號回蕩在中國大地。五四運動爆發了。
當天就有32 名學生被捕,卻因此引起人們更大的不滿。各地群眾風起響應,從學生罷課發展到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其他群眾團體也紛紛成立各種社會力量直接行動起來干預政治,在億萬順民中突然爆發出強大的憤怒,整個中國沸騰起來了。
6月5日,上海工人罷工,人數超過2萬人。幾天后達到五六萬人,使海陸交通為之中斷,舉凡運輸、印刷、鋼鐵、紗廠、土木、車夫全部罷工,甚至連娛樂場所也都停業。
陳獨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強調“強力擁護真理,平民征服政府”,結果在散發傳單時被捕。周恩來率天津學生赴北京請愿……
這是一個時代的呼聲,也是古老中國對中國青年的呼聲。
在法國巴黎,面對北洋政府同意簽字的命令,中國代表團也在激烈地辯論。時年30歲的年輕外交官顧維鈞說:“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山東形勢關夫全國,較東三省利害尤巨。不簽字則全國注意日本,民氣一振。簽字則國內將自相紛擾。”5位全權代表中3人反對簽字。
6月28日,在《巴黎和約》的簽字現場,人們驚奇地發現中國代表團的席位上空無一人。這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第一次對列強說“不”。此時的顧維鈞正乘坐汽車經過巴黎的街頭,他用自己的方式表示了憤怒。
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意味著中國人民的覺醒,但整個政治局面依然一片黑暗。“中國往何處去”這一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使人們感到緊迫,也使人們感到迷茫。
就在中國代表團拒絕簽字的幾天后,蘇俄發表《對華宣言》,聲明將廢除對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歐洲,尤其是蘇俄的現實使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探索一條新的道路。(文稿校對:見習記者王湘媛)
文章出處:人民出版社、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復興之路》
責編:瘦馬 編審:王輝 終審:盧子璋